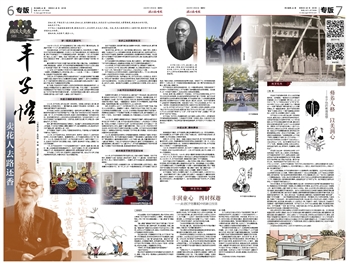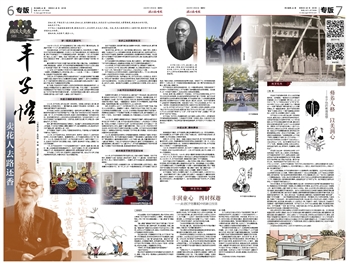□陈 星
评说丰子恺的教育思想,可以从他的两幅画谈起。这两幅画,一幅是他为立达学园画的校徽图案,为三个幼童拥着一颗大红心,红心正中为“人”字,“人”字两边分别为“立”和“达”字,充分体现了立达人凸显、强调的“立人”教育理念——本源于教育者一颗赤诚的育人之心的教育理念;另一幅画是《教育》,是丰子恺讽刺某种“教育”只是像工匠在一个模子里铸造出相同的泥人,没有个性,没有精神,更谈不上创造。
丰子恺自1919年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曾有过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经历,这段经历因他赴日本游学而中断;1921年冬回国后,他于次年应邀赴春晖中学任教,最终因与学校当局的教育思想不合而于1924年年底辞职。辞职后,丰子恺与匡互生等人一起于1925年年初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后改名为立达学园。经验让丰子恺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就必须走一条自己开创的道路。合作者匡互生说得更具体:“如果要坚持呢,必不见容于学校;如果默尔不言呢,良心又不允许他……”他们创办的学校取义《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句。他们的教育关注点乃在于“人”本身。围绕着立达学园,也有立达学会,其宗旨是“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
早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丰子恺即具备了修养人格、以美润心的思想基础。丰子恺随李叔同学习艺术,成绩出类拔萃,但李叔同给予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情操和艺术修养等方面,即给予他的是一颗艺术家的心灵。李叔同告诫丰子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使丰子恺意识到:“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描画吟诗,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则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械了。”
有了上述思想基础,丰子恺在教育实践中十分强调修养人格的重要性。立达中学正式更名为立达学园的时间是1925年夏。同事朱光潜执笔写了一份《立达学园旨趣》,公开了改名立达学园的原因,其中就明言:“我们坚信学校要有特殊的精神,才可以造就真正的人材。”“我们的人格教育第一个要素就是诚实。”这种人格为先的教育思想,用丰子恺为立达学园所绘的校徽图案即是那个“人”字,而铸就这种人格的教育者的精神,也就是两边的“立”字和“达”字。他们希望自己培养出的学生,个个都是赤子般的诚实之人。
作为艺术教师,丰子恺也同样践行着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莫如提倡美育”的主张,希望能在自己的学校里辟一块园地,来从事真正的艺术教育,设立艺术科,欲在立达这一块园地上作一番艺术的耕耘,这跟“学园”这个词也十分吻合。其实,立达中学之所以要改名为立达学园,很大程度上跟该校重视艺术教育有关。他们认为把校名改成立达学园才能够表示教育的真正意义。因为教育的真正意义是引发而不是模造,是要使被教育者在能够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发展,这正像园艺家培养花木一样。故此,匡互生说:“无论教育者,被教育者,大家都把学校看做‘美的世界’,看做‘艺术的宫殿’……我们希望教育者有真正的园艺家一样的趣味,所以叫学校做学园,凡是花园,又是极广大极自由的。其中各种形形色色的花草,无论是大的小的红的白的,本国的、外国的,都可兼收并容,各自发展,学校培养人才,也该和这一样,不能拘于一格的。”这种主张,又恰是丰子恺《教育》一画所希望表达的教育思想。丰子恺又以为,艺术不仅仅是绘画、唱歌,而主要是生活的艺术。丰子恺强调:“‘生活’是大艺术品。绘画与音乐是小艺术品,是生活的大艺术品的副产物。故必有艺术的生活者,方得有真的艺术的作品。”
至此,或许还可以用朱光潜将人们对待外在世界的方法区分为三种态度来小结。这三种态度就是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他认为“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其实,这种以“人”为关注对象,并进而以此为目标在文艺、教育、出版等各个领域展开自己踏实的工作,切切实实地为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贡献自己一分心力的态度与作风,是我们在从事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工作中可以强调与借鉴的;在一个日益技术化的时代,这种直接将教育的终极目标定位在“人”本身的思想,进而又以美来加以浸润的方式,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工作中,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