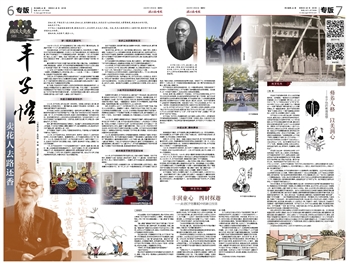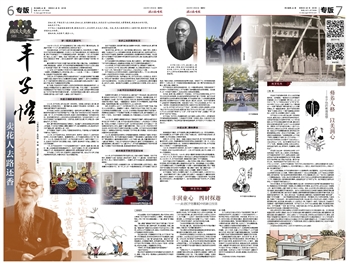□本报记者 朱诗琪 金 澜 实习记者 邓昊冉
在他之前,中国没有人这么画画;在他之后,虽然模仿者甚众,但是没有人达到他的高度,仅寥寥数笔,便能画出世间万象。
他就是丰子恺。
丰子恺从小就被脉脉温情包围,暖意来自家人、来自恩师、来自友人同道。而他,更是以温柔悲悯之心看待万物,落到笔下便是充满诗意的生活场景。
看他的画,泪在眼中,暖在心头。
梦一般的儿童时代
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在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市石门镇)呱呱坠地。因是家中的第一个儿子,被长辈视若珍宝,故取乳名“慈玉”。
丰家是染坊世家,丰子恺的父亲中举后做私塾先生,在世时极受人们尊敬,而丰子恺的母亲在遭遇婆婆、丈夫和几个孩子离世等变故后,努力维持染坊生意,帮丰子恺保留住了一个充满温情且如同梦一般的童年。儿时,丰子恺曾跌到门槛上,头上留了一道疤。他说:“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
童年时期的丰子恺有三件最不能忘却的事:养蚕、吃蟹、钓鱼。如果要算第四件事,那就是绘画。说起来,丰子恺初学画的故事跟普通孩子并没什么区别,都是从“乱涂乱画”开始的,唯一不同的是,丰家经营染坊,讨要颜料更容易些。
七八岁时,丰子恺觉得《千字诗》中的大禹耕田图有趣,就从染匠那里要来了一些颜料,用笔蘸着给书上单色的画上色——一头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色的地,这就是丰子恺绘制的第一幅画。
从那之后,丰子恺就被这多彩的绘画世界迷住了,他会躲在扶梯底下画、瞒着私塾先生画,绘画的内容也从临摹到原创肖像画。画得多了,画作也变得精美起来,不少画作被同学讨要贴在灶头间或床头,就连私塾先生都让他绘制了一幅大型孔子像,贴在了私塾堂前供学生拜谒。
除了绘画,开启幼时丰子恺美术之旅的还有两样东西,那就是玩具和花灯,尤其是红沙泥模型和花灯会,最能引起丰子恺的兴趣。竹龙、泥猫……各式各样的印泥模型给丰子恺“视觉以充分的粮食”,而在彩伞上刺绣、绘制画作等制伞流程给了丰子恺“美术制作的最初的欢喜”。在《视觉的粮食》这篇文章中,他发出这样的感慨:美术是人生的“乐园”,儿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
负笈求缘的苦学经历
1914年,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学音乐、做文章、接触西洋画、去西湖边写生……最关键的是,他遇到了两位影响一生的恩师——慈母般的夏丏尊和严父般的李叔同。
丰子恺读二年级时,正好是李叔同教这一届学生学木炭石膏写生。第一次接触西洋写生画的丰子恺对西洋画产生了兴趣,而他飞快的进步也引起了李叔同的注意。有一天,丰子恺有事去见李叔同,告退时,李叔同郑重地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这句话对当时才十七岁的丰子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那天起,他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
彼时,夏丏尊在学校既是舍监又教国文。他会毫不心软地当面指出学生思想上的偏差,不允许他们有懈怠、萎靡、懒散的习气,每日都要积极上进;批改学生作文时“锱铢必较”,斟字酌句,逐一点评。
丰子恺曾说:“我倘不入师范,不致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致学画;也不致遇见夏丏尊先生,不致学文。”
1919年,丰子恺顺利毕业,和同学刘质平、吴梦非一起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自任美术课教师。随着教学深入,丰子恺越发觉得自己在“闭门造车”。1921年,在亲戚们的支持下,丰子恺东渡日本学习。虽然只停留了十个月,但是丰子恺的学习涉及素描、油画、小提琴、语言等多个领域,还邂逅了自己的灵感缪斯。
一天,丰子恺在东京的一个旧书店里偶然见到了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随手一翻,立刻被里面的简笔漫画吸引了。在丰子恺看来,竹久梦二的画风熔东西洋画法于一炉,其构图是西洋的,画趣是东洋的,称赞其画是“无声之诗”。
丰子恺陷入了对竹久梦二的崇拜中,回国后热度不减。他也从竹久梦二的画风里得到许多启发,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漫画风格。
漫步山水的教师生涯
当丰子恺回国时,恩师夏丏尊已经在春晖中学任职。听闻学生归来,夏丏尊就写信约他前来共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创作于1922年的春晖中学校歌,歌词取自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曲子则由丰子恺谱写,旋律简单,如同涓涓细流,流淌着纯净质朴的情感。而这首曲子也代表着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教时的生活状态和心境:在远离尘嚣的白马湖畔,一心钻研美育。
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主要教音乐与绘画,偶尔也教英文。夏丏尊曾对学生说:“丰子恺先生真是全材,他能教音乐和图画,我们不好意思再请他教别的了。”
1924年年底,丰子恺因与学校当局的办学思想不合,辞职离开了春晖中学。
1925年年初,丰子恺、匡互生等人凑钱筹款,在上海租用民房创办了立达中学。“立达”二字,乃取《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
丰子恺担任立达中学的校务委员,也是西洋画科负责人。不久后,学校还增办高中,并设农艺科和艺术专修科,改校名为立达学园。
立达学园的宗旨是:“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学校主张“爱的教育”,即师生住同样的宿舍,同桌吃同样的饭菜,用说服、感化的方法来教育学生。在这种优良的教育方式下,立达学园很快以教学质量闻名,成为沪上名校。直到淞沪会战爆发,立达学园在战火中损毁,多年心血付之一炬。
为孩子们创作的艺术家
在春晖中学任教时,丰子恺在校务会上随手画下了神态各异、垂头拱手的同事,画完后又恐学生见了不好,便把这些画贴在了门的背后。端详着这些画,丰子恺兴趣盎然,之后便一发不可收,包皮纸、旧讲义纸、香烟壳的反面都成了画纸,有毛笔的地方就成了画室。一幅幅画就如一首首诗,平凡中带着奇特,浅显中带着深奥,风韵独特地展示着人世间的琐碎平凡,让人回味无穷。
当时,朱自清与人合办了一份刊物《我们的七月》,他向丰子恺要了张画,刊登在1924年的期刊上。那幅题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画,引起了在上海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注意。1925年,《文学周报》开始连续刊载丰子恺的画作,郑振铎给这些画定了“子恺漫画”的标题。《子恺漫画》的出现,是中国漫画步入正轨的一个标志。在这中国第一本漫画集之后,中国绘画史上才正式有了“漫画”的命名。
1926年8月,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创办了摒绝官气市廛气、倡导自由新风的开明书店,取“开宗明义”之意,丰子恺亦是当时的支持者之一,并主持设计了开明店徽。“淡观山水闲看月,只读诗书不念愁”,在开明书店任职时,丰子恺度过了一段怡情悦性的读书人时光,编著了大量书籍和刊物。例如1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杂志,创刊号中有丰子恺美术讲话四篇、补白两篇。丰子恺作为该杂志的重要作者之一,每期都会发表作品,内容涵盖了艺术讲话、散文和漫画。该杂志也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读物。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国语》,明确规定了编写小学语文教材的诸多条例。其中在教材编选方面提到了“要依据增长儿童阅读能力的原则”“要依据增长儿童阅读趣味的原则”,以及“依据儿童心理,尽量使教材贴切于儿童生活”等要点。于是,丰子恺和好友叶圣陶合作,编写了《开明国语课本》。这套民国老教材,真正做到了“以儿童为中心”,丰子恺的童趣插画和不同字号的挥毫,不仅增强了书本的阅读乐趣,更是绝佳的美育和书法范本。
爱的教育不拘于空间地域
1933年,丰子恺用版税和开明书店的分红,在家乡建造了缘缘堂。在丰子恺眼中,缘缘堂不仅是一座供家人居住的房子,更是一个儿童乐园。他在院子里安装了秋千,种上了缤纷的花草树木。一到夏天,孩子们放假归来,缘缘堂就变得热闹起来。
丰子恺是艺术巨匠,也是慈爱的父亲。他习惯言传身教,会用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方式教育子女。有一次,女儿丰一吟随便踩蚂蚁玩,丰子恺看到了连忙劝阻说:“蚂蚁也有家,也有爸爸妈妈在家等它回家。你踩死了它,它的爸爸妈妈就要哭了。”从那以后,丰一吟每逢见到蚂蚁搬家就会拿一些小凳子放在蚂蚁经过的路上,提示过路人绕道行走。
丰子恺成名后,经常收到读者来信。丰一吟喜欢帮他拆信,习惯性地把拆下来的那片小纸条随手扔地上,丰子恺看到了就弯腰拾起来放进纸篓里。如此数次,丰一吟有些不好意思了,此后主动把小纸条放进纸篓里。
在丰家,每周六晚上都要召开一次家庭会。丰子恺会买些糕点果品,孩子们可以边吃边听他讲故事,这也是丰家独特的家学传统“课儿”的来源。基于对古诗词的热爱和对古诗词句教育功用的理解,丰子恺逐渐将“课儿”从讲故事发展到教授古诗词,他的教学方法也十分特别:画出来,唱出来,玩出来。在丰子恺的影响下,家里的学习氛围特别浓厚。饭前游戏飞花令、节日必玩览胜图,孩子们一面玩,一面欣赏、交流游戏背后的典故和诗词,在游戏中充分享受诗词的化育。
1947年,丰子恺又与子女们立下“约法”。其中第四、五两条尤其独特:让已经“独立”的子女过自己的生活,鼓励已经“独立”的子女与父母“分居”;子女独立了,父子父女之间也就不再有什么“义务”,只有“友谊”和“邻谊”,这超越了“养儿防老”和“长宜子孙”的观念。
丰子恺说:“孩子的心灵是最纯洁的,他们是身心全部公开的人,好的教育和坏的教育都很容易被接受。父亲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因此,父亲对孩子们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有这样的家风影响和家教培养,丰子恺的七个子女都成了有用之才。
师道永存,精神赓续
缘缘堂里岁月静好,丰子恺就想过着这样晴耕雨读的人生。然而世事难料,抗日战争爆发后,丰子恺携一家老小开始了逃难之旅。当时的中国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目之所及都是人间炼狱的画面。
悲愤之中,丰子恺一路走,一路画:他画自己变成天使,挡下空中的炸弹;他画鲁迅的《阿Q正传》,希望唤醒百姓的觉悟与深省;他画祖国的一草一木、大好山川,那是他所展望的美丽人间。在那段充斥着硝烟和鲜血的日子里,丰子恺用画笔为人们构筑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桃花源。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又创作了三幅画及《狂欢之夜》一文,慨叹“一觉起来,欢迎千古未有的光明白日”。之后,丰子恺定居上海,专心译著,1975年9月因病逝世。
先生千古,风范长存。1984年,被炮火摧毁的缘缘堂在原址按原貌重建;1985年9月15日,即丰子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新筑成的缘缘堂举行了开馆仪式;1998年11月,丰子恺百年诞辰,缘缘堂东侧又建起了丰子恺漫画馆。
在丰子恺家乡的丰子恺漫画学校——桐乡市凤鸣小学里,学生们习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手中的画笔、颜料以漫画的形式记录下来。学校信奉童心文化办学理念,以《子恺漫画》为指引,不仅每学期设置八个主题十六课时的漫画拓展课,开发了“漫画四时”校本课程,校内还有丰子恺漫画苑、“童心漫画”大课间、“童心漫画”社团……不断引领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在他们心中播撒一颗颗艺术的种子。
丰子恺曾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在他的精神引领下,桐乡乃至整个浙江涌现了一批批爱孩子、懂教育的浙派名师名校长,就像丰一吟在《他留下一条芬芳的道路》一文里写的那样:“在这条道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他们争相吸取他留下的芬芳之气,采摘他播种的花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