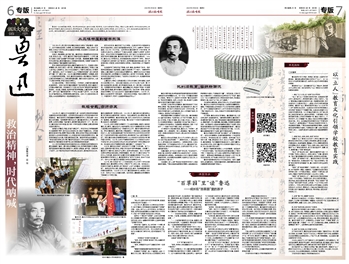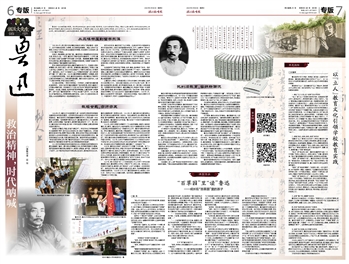□本报记者 汪 恒
鲁迅的一生与教育缘分深厚。作为学生的他先后入读旧式私塾、洋务学堂,又在日本修读专门学校。鲁迅又主要以教育工作作为其社会职业,他曾历任中学教师、教务主任和校长,师范学校校长,大学讲师、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等各种职务,共计18年之久。此外,他还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过8年。教育在鲁迅眼中,也是改造国民精神、唤醒民众的途径。要走近和理解鲁迅,就不能不提他作为教育家的一面——
从三味书屋到留学东瀛
1881年9月,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喜添一名男丁。孩子先得幼名阿张、长庚等,后又得学名周樟寿。周家人或许不会想到,日后这个孩子的出息会远超他们的想象,而且更多人记住他的,是一个叫“鲁迅”的笔名。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此时还在京城为官,官至正七品。7岁时,鲁迅进了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12岁时,鲁迅又被家人送到“全城最严厉的私塾”三味书屋。高高瘦瘦、戴着大眼镜的先生寿怀鉴,课间的嬉戏逗乐,百草园的四季流转,与保姆“长妈妈”的相处点滴都成了鲁迅童真时光里的回忆。
然后,接连而至的波折很快让鲁迅的童年失色不少。先是祖父因科举舞弊入狱,后来父亲又一病不起。家境败落让鲁迅感叹,“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回忆,自己“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但父亲的病却“日重一日”,最终亡故。1898年,鲁迅带着母亲筹得的八块银圆,孤身一人去南京读洋务学堂。当时,鲁迅的远房叔祖父周庆藩在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又兼任管轮堂监督。鲁迅也因为这层关系,入读了江南水师学堂,并将大名改为周树人。
在江南水师学堂,一周四天学英语,一天学语文,功课内容在鲁迅看来是简单的。来到大城市的鲁迅接触到了更多新思想,闲时也翻起了《天演论》等新书报。来到南京几个月后,他又投考了新设的矿路学堂并被录取。在这里,有德语、地质学和矿物学等课程,让鲁迅觉得“非常新鲜”。采矿也成了鲁迅修读的第一个专业,他也曾下过矿井。1902年,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并获得官费出国的资格。这年3月,他告别母亲,和同批20余名官费留学生一起坐轮船前往日本。
到日本东京后,鲁迅先进了弘文学院。这是当时专为中国留学生举办的速成学校,主修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为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基础,1902年1月才开设。这所学校在鲁迅看来多少有点奇怪,学生要去孔庙行礼,还要执行“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这样的规定。学生们和校方的摩擦时有发生,因不满日方对留学生的升学规定和学校课程设置,鲁迅就目睹并参与了两次罢课活动。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决定继续就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缘由多少和童年时父亲的病久治不愈有关,他梦想着回国后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又能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开设了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等多门科目。很多医学名词都是拉丁语或德语,让鲁迅记起来费了不少脑力。在解剖学的课堂上,鲁迅遇到了让他终生感念的藤野先生。藤野先生对这位中国留学生很是关照,主动帮鲁迅订正课堂笔记、询问学习中的困难。鲁迅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叹,“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让鲁迅决心转变人生轨道弃医从文的也许是第二学年课堂上放映的几张时事幻灯片。当时正值日俄战争,幻灯片中出现了这样一幕:中国人给俄国军队做侦探,被日军捕获并枪毙,而一群中国人在现场围观。在周围同学的拍手喝彩中,鲁迅清醒过来,学医学不再是一件紧要的事,国民的愚弱、麻木的看客心理更加可怕。“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这个念头此后长久盘旋在鲁迅的脑海中。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他告诉好友许寿裳,“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教坛廿载,亦师亦友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到国内,第一站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学和化学两科的教员。这所学校的校址就在今天的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鲁迅当时的工作就是翻译日籍教师的讲义,同时也教一点生理卫生的课程。在同事夏丏尊的记忆中,鲁迅翻译的讲义,不仅被同事称赞,也受学生尊重,“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第二年8月,鲁迅应绍兴府中学堂(绍兴第一中学的前身)的聘请,去教生物学兼任监学(教务长)。
回到家乡的鲁迅,先碰上的是“无辫之灾”。早在日本弘文学院就读期间,他就剪掉了辫子,绍兴这边认识他的人多,因此不免遭到议论。好在随着辛亥革命的开始,剪辫不再成为问题。新成立的绍兴军政分府任命鲁迅担任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更名为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鲁迅有时候自己也代课,代国文教员批改文章。据当时的学生孙伏园回忆,“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许寿裳向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蔡元培也早慕鲁迅之名,欣然请许寿裳代为邀请。再次回到南京的鲁迅想必感慨万千,新身份、新国家、新气象。在南京待了没多久,由于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妥协,国民政府迁往北京。鲁迅也随教育部一起转往北京。1912年8月,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后又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在社会教育司,他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项。鲁迅的官场之路,在外人听来风风光光,但背后是另一番景象。鲁迅曾在日记中写道,“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致聊赖”。
1920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想新开一门小说史的课程,系里的人就找到鲁迅,送上聘书。鲁迅对古代小说早有研究,在北大任教期间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后来更是被视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鲁迅的课极受学生欢迎。学生王鲁彦回忆,鲁迅的课上“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连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同时,鲁迅也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聘作国文系讲师。1923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后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和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也聘他为讲师。而正是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鲁迅遇到了一生知音许广平。
1926年,鲁迅自北京南下,前往创办不久的厦门大学任教。除了小说史,还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等课程。初到厦门,鲁迅听不大懂方言、饭菜也不合胃口,但学生待他甚好。有几个本地学生周末还带他去城区游玩,并陪同做翻译。第二年1月,鲁迅又前往广州的中山大学任教,甚至还有几名厦大的学生跟着他转学到了中山大学。春季学期的开学典礼上,鲁迅鼓励学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在中山大学,鲁迅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山大学不少学生也惨遭逮捕、枪杀,鲁迅辞职以示抗议,并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政、教两界,我不想涉足”,以后“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吧”。虽然此后并未从教,但鲁迅仍通过社团、演讲、书信等激励着当时的青年奋勇抗争。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有多达7000人为鲁迅送葬。他的灵柩上覆盖着由沈钧儒题写“民族魂”三个字的大旗。
批判旧教育,容纳新潮流
鲁迅对清末通过科举制度培养官僚和国民政府时期奴化教育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许广平在一次和鲁迅的通信中,问起他,“教育对于人是有多大的效果?”鲁迅在回信中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
在目睹了当局对学生的屠戮后,鲁迅深刻剖析了旧式教育之弊端,“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都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
要改造国民精神,改造教育乃当务之急。鲁迅强调回归儿童天性的教育。“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鲁迅认为,旧式教育的弊端之一就是把青少年当成“缩小的成人”,不注意他们的年龄特点。“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一向就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
对于教育中父母扮演的角色,鲁迅认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鲁迅觉得,不应用一种模式来限定孩子的成长,要让他们的天性得到完全的释放。
鲁迅还从进化论的角度,否认父子之间有什么恩,认为生儿育女完全是自然规律。“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对于封建观念中的父子之伦,鲁迅直言不讳:“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在鲁迅看来,孩子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体。“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
在他看来,育儿上要“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有的家庭,父母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父母美其名曰这样的孩子才“听话”,鲁迅认为:“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旧式教育注重读经,教育内容也与人的全面发展相悖。鲁迅在北大给学生作讲座时说,大家要时刻懂得劳动、健康,不得像封建社会的那些女子认为纤细柔弱才是最美的。孩子们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反映出了整个国家的水平。因此,加强孩子们身体素质的培养决不能够放松。
对于美育,鲁迅也有自己的看法。鲁迅喜爱木刻,儿时还学过美术,偷偷做指甲戏。在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指出“美育是感性与趣味两种教育的结合,美感的提升,可以温煦情感,陶冶情操,为单调的生活增加色彩。我们国家的人都是在封建教育的模式下生活的,因此现在的美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较重要的影响”。鲁迅还建议给孩子们开办美术展览,来增加他们的兴趣。1914年,鲁迅全程准备并参与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活动。
鲁迅主张教师对学生要“绝无傲态”,应“和蔼若朋友然”。他在北京任教期间,总是热情地接待每一个来访的校内外学生。学生给他去信,他一定复信。有学生拿了自己写的文章、书稿,请他批改、校对,他也从不推辞。对于青年,鲁迅曾寄语,“你们最富有的就是生命力,这种力量可以将丛林夷为平地,这种力量亦可以在荒芜中造就大片的丛林,可以在沙漠中寻求生机”。
鲁迅对于理想的教育模式,心中自有憧憬。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件中提到,“我们现在所应用的教育模式,不管对于哪一个国家来说,也不过是从逐渐的符合环境的生活方式算了。要想说话办事都能够合适,张扬每个人的个性,现在还没有实现,也不知道以后我们会不会可以实现”。
鲁迅的很多教育观点在今天仍有启发性。他的儿童教育观、家庭教育观、大美育观富有洞见,激励着教育改革者向着理想的教育图景不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