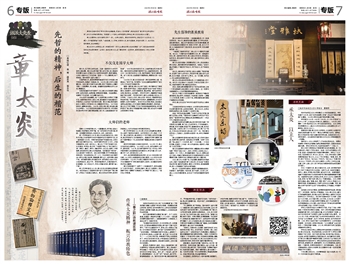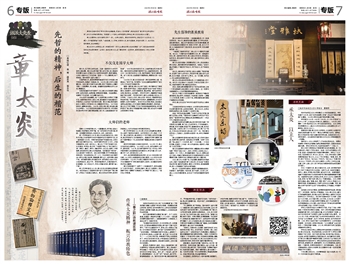□本报记者 张 莺 通讯员 张自恒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学者、朴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哲学、政治、朴学等,一生著述甚丰。
周恩来总理评价他“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是浙江人民的骄傲”;胡适说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当代文史学者刘梦溪说,“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一生特立独行。鲁迅是他的学生,曾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其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章太炎为什么获得这么多人的高度评价?是什么让鲁迅对章太炎如此尊敬?当下,我们该如何传承他的优秀品质和精神?让我们一起走近章太炎,在了解他传奇一生的同时,感受他留给世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不仅仅是国学大师
章太炎,生于浙江余杭仓前。这是一座具有800余年历史的江南古镇。章太炎出身书香门第,世代行医,祖父章鉴有许多藏书,给幼小的章太炎以无穷的知识滋养、浸润与熏陶。6岁时,他就吟出了平生的第一首诗——“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
为培养章太炎,具有深厚国学基础的外祖父朱有虔从海宁来到余杭,在章家一住就是4年。1890年,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去世。此后,章太炎离开仓前古镇,来到了西湖孤山之麓的书院——诂经精舍,师从俞樾。俞樾曾在诂经精舍主讲30余年,博通经史。
在恩师俞樾的引领与指导下,加上章太炎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他进步很快,成绩卓著,深得老师的喜爱。在诂经精舍,他撰写了平生的第一本书《膏兰室札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给一心治学的章太炎带来了沉重打击,他断然离开杭州,前往上海,参加康有为与梁启超创办的强学会,从此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章太炎通过报纸宣传革命,以激发人们的革命斗志,唤醒更多的民众。1897年回到杭州,编辑《经世报》。1898年,应张之洞之邀,前往湖北筹办《正学报》。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3年,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1906年出狱后前往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晚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章太炎一生办报先后多达15种,很好地宣传了革命与教育思想。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学习。
1936年6月,章太炎在临终前一周仍坚持带病上课。他曾说过:“饭可不食,书仍要讲。”这也正是教育家精神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典型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从来不是在一种平静状态下接受某一思想(或学术观念),而始终是坚持“依自不依他”的独立意识,在争辩中、对抗中选择取舍,融合贯通。章氏治学讲求自得,既反泥古,也反媚外。评判历代学术,其重要标尺就是能否“独立自得”。而对西方学术,章氏从来都是以我为主,不为所拘。上世纪20年代,章太炎有一段自白,很能表明他这种治学风格:“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色彩。”章太炎之不同于清儒,不只在于他有幸借鉴泰西学说,学术眼界更为广阔;更在于其超越考据,直探义理,成为近代中国真正有思想的大学者。
大师们的老师
身兼斗士与学者的章太炎,一生屡遭世变,多次卷入政治斗争旋涡,可依然著述、讲学不辍。他一生先后有4次比较大型、持续、一定规模的讲学活动,分别在日本、北京、上海与苏州。
第一次讲学是在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前往日本,当年秋天开始,为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办国学讲习会,并一直持续到1909年。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话,以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为主。当时听课的学生有100多人,多是中国留学生,也有一些日本人。章太炎门下弟子有诸多大师,比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父亲)、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鲁迅弟弟)、沈士远、沈兼士、许寿裳等,都在那时听过章太炎讲座授课。当时著名的“周末班”,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办的。回忆当时的情景,弟子许寿裳是这样表述的:“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
第二次讲学是在1913年,章太炎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时。他在写给夫人汤国梨的信中说“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并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的此次讲学,前来听讲者甚众,大多为京城各大学的教员和学生。
第三次讲学是在1922年,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在上海作了国学系列演讲。此次讲学共10次,持续一个半月。章太炎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根据此次讲学,曹聚仁编成了《国学概论》一书,此后由张冥飞整理出版《章太炎国学讲演集》。
第四次讲学是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时。1933年1月,章太炎在苏州成立国学会。1933年至1934年,他先后演讲20多次,盛况空前。1935年,自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为私人学校作国学演讲,由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生中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
另外,他还接受邀请到各地讲学,如1901年在东吴大学任教,1903年在上海爱国学社任国文教员,1925年在长沙辰光学校演讲。1926年6月任职上海国民大学校长,1933年3月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演讲《国学之统宗》,在无锡师范学校讲《历史之重要》。
章太炎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弟子,因而也被称为“大师们的老师”。在讲学过程中,章太炎“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和“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一直为世人所称道。
先生倡导的素质教育
章太炎将学问分成两类:一类是基础知识,另一类是应用知识。他认为,基础知识最为重要,对于学生来说,是发展的根本。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和整理,章太炎将基础知识概括为书(语言文字学)、数、史三大方面,认为基础知识学了虽没有用,但也应该学,而且是教育的第一步。
“书数通了就要讲历史”,章太炎十分重视历史教育。他认为,“大概历史中间最要的几件,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辞的变迁,都在志和传里头”。
章太炎生活在国家、民族濒临危亡之秋,因此他提出要以史育人,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他指出:“欲成大器必先通史,不通史而不知古今,而不知古今,且不知经世致用。”
他认为,青年学生不学历史,就无从爱国。“现在的青年,应当明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全部找到明确的指示。”
章太炎从民主革命的思想出发,大力提倡发展人的个性。他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个性,才能孕育新的大群,推动社会的进步。
因此,他提出教育要重视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思想与当前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高度吻合。
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一直受到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观念保守、内容陈旧、方法机械、目标单一,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个性,使得受教育者的潜能不能得到充分的挖掘。
然而,章太炎也反对“学问专为致用”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念。
尤其是在洋务派创办学堂后,以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全面否定国学。章太炎认为,这样会把学生培养成工具,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价值。
他说:“学问本来是求智慧。”“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致用的学问未必真能合用;就使真能合用……机会不巧,讲致用的还是无用。”
教育要开启学生的智慧,就必须对学问进行创新。“学问既然为求智慧,得了前人已成的学问,不可将就歇手。要知道,知识与道德,原是不同;道德或者有止境,知识总是没止境。以前的人积了几千年的知识,后人得了这个现成,又发生自己的知识来,就比前人进了一级。现在看当时的后人,又是前人,应该要比他更进一级,学问才得新新不已。”
章太炎把教学形象地比喻为做买卖,前人的学问是本金,创新的部分是利息,也就是自己的智慧。如果不去创新,“那么就求了一千年的学,施了一千年的教,一千年后的见解,还是和一千年前一样,终究是向别人借来的,何曾有一分自己的呢!”
章太炎在提倡常识教育的同时,着重提出常识也需要创新:“常识不是古今如一,后来人的常识,应该胜过古人,但要求一代一代的人,常识辗转增进。”他认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教育者在学问方面要有独到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教学方法上要做到化难为易、化繁为简。
为此,章太炎从发展个性、开启智慧、掌握常识的角度出发,突破了传统教育所谓“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的教育观念和内容,重视历史教育,增进人们的常识,培育爱国精神,把个人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章太炎一生坚持常识教育,提倡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发展智力、培养道德、大胆实践、敢于创新,从本质上讲,是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放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